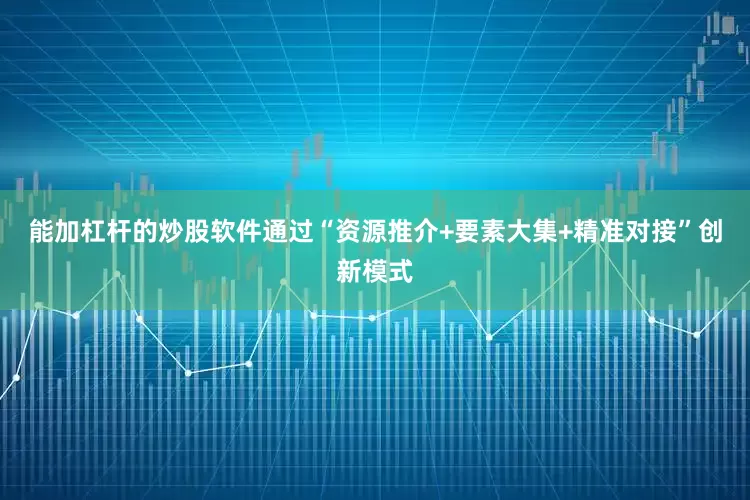这封宋庆龄女士的书信,对于深入理解潘汉年案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。历经岁月的沉淀,该信件首次于《家国梦萦——母亲廖梦醒与她的时代》一书的修订版中与世人见面。李湄,系著名历史人物李湄之女,亦为廖仲恺与何香凝的直系外孙女。1932年,我出生。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会员,以及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。1954年,我踏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大门,随后在新华社担任俄语翻译工作,并在中国电影家协会专注于英美电影的研究领域。
在我母亲收到的宋庆龄女士的信件中,有一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3月17日所写的那封。起初,我对这封信的关注点仅限于其中提及潘汉年的内容。潘汉年与我的母亲交情匪浅,然而,他在1955年因涉嫌反革命罪被突然逮捕,这一事件的真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界都保持着神秘。
我始终困惑,为何毛泽东昔日对潘汉年深信不疑(毛泽东早年的一部传记,书名便是潘汉年所题!),却最终对他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态度。信中露出端倪。
往昔,我们对党史的诸多细节一无所知。然而,近年随着共产国际解密档案的逐步披露,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逐渐浮出水面。当我偶然翻阅到宋庆龄于1937年1月致王明的信件时,不禁发现,若将此信与我母亲所收宋庆龄的另一封信件相互参照,便能对一些疑惑之处寻得解答。

茅盾、夏衍、廖承志;后排自左而右则是:潘汉年、汪馥泉、郁风、叶文津、司徒慧敏(摄于1938年3月29日,广州)。
下面是宋庆龄致王明的信中引起人们注意的两段话 (生成长度超过限制(9.3 倍))(源自2008年6月3日《作家文摘》邵雍与刘雪芹的《揭秘宋庆龄致王明的密信》)当时,宋庆龄已投身共产国际的怀抱,而王明则担任她的直接上级。
“不久前,针对毛泽东同志寻求资金援助的来信,我在三个月前已寄出相应款项作为回应。此事仅有一人知晓,他担任联络人的角色,经由他,我得以接收信件并转寄款项。”在1936年,毛泽东经由潘汉年的牵线,向宋庆龄寄出了一封书信。宋庆龄在收到信件后仅一个月,便委托潘汉年将款项转寄过去。”
数周前,宋子文在获释蒋介石承诺后返回西安,他希望能与我见面……宋子文当时向我提问:“若我向你透露,周恩来曾告知我,你近期曾向他们汇去了五万美元,你还会坚持否认你的同志背叛了你吗?”
两段陈述引发了以下两个疑问:首先,周恩来为何要将宋庆龄资助中共的款项一事告知宋子文?其次,宋庆龄所寄给毛泽东的款项是否出自其个人财产?这两个疑问在宋庆龄于1969年3月17日致我母亲的信中均有提及。
“潘汉年于被捕前半年将那笔款项交予我,我起初误以为他意图利用我,遂嘱托隋同志——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——将款项转交予某人。此人,我曾在黄敬担任天津市市长时于天津有过一面之缘,但已忘却其名。他是一位军人,在潘汉年与柯庆施自南京调任上海之前,曾掌管上海事务。对了,他的妻子是广东人。(母亲在空白处填上了“许建国”的名字。)隋同志送钱时,他正身处会议中。隋同志向他告知,这笔款项是潘汉年所送,并称其为毛主席‘偿还的款项’。他即刻将潘汉年自会场召回。潘汉年在隋同志面前详细解释了这笔款项的来由。这并非用于归还‘为党所需’所借之款项,而是用于归还毛主席请我向宋子文借款之事(他不知情,自1927年我赴莫斯科后,宋子文便与我分道扬镳)。不久,那笔曾是我生计所依的钱款再次返还于我。我写下这些,旨在向你说明,‘董牧师’从我手中取走的并非那笔特定的款项……
“正是王明,他从莫斯科发来电报,指示我不再与董牧师见面,而这封电报,是由董牧师的女儿露西亲手送达的!”
在上述段落中,宋庆龄阐述了三个要点:首先,那笔款项系毛泽东所委托,她向宋子文借款所得;其次,鉴于彼时她与宋子文已分道扬镳,不便向他借款,故此款项乃是她个人所出,此乃她昔日赖以维生的资金;再者,“董牧师”曾擅自取走她部分资金,之后王明劝诫她不再与“董牧师”相见。

首先,这一问题源于1937年宋庆龄致王明的信中所提出的首个疑问。为何周恩来会将宋庆龄汇款一事告知宋子文?这是因为周恩来知晓毛泽东曾请求宋庆龄向宋子文筹措资金。与提供资金的人交流借款事宜,理应顺理成章。无非是告知宋子文“款项已接收”而已。尽管宋子文在1936年已卸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,但他依旧被视为中国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。通过其姐姐从中斡旋,向宋子文借款应属可行。当时,共产党刚刚长征至延安,经济状况极为困难,因此采取此措施。周恩来并未预料到这笔资金实际上与宋子文无关。事实上,周恩来以及毛泽东或许一直以为这资金由宋子文提供。直至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,潘汉年偿还宋庆龄款项时,仍旧称之为偿还“毛主席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的钱”!宋庆龄未曾意识到,引发这场误会的正是她本人。若当时她直接向中共透露款项并非宋子文所提供,这场误会便可避免,宋子文也便无机可乘地利用此事来挑拨她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。
宋子文的话语对宋庆龄产生了不良影响。1954年,潘汉年将“毛主席退还的款项”转交给她时,她误以为潘汉年意图“利用”她,因此指示隋秘书将这笔款项退回。非但未将款项直接退还给潘汉年,反倒是转交给了当时负责公安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。面对许建国的紧追不舍,潘汉年无奈之下,只得在许建国与隋秘书的见证下透露:“此乃毛主席所托,宋庆龄向宋子文所借之款。”如此党内机密,竟就此公之于众。这非毛所愿。半年后,潘汉年被捕。导火索虽非此事件,但这事件或许也成了他不幸命运的一触即发之因?
在宋庆龄女士致我母亲的信中,反复提及的“董牧师”实则是一场误解。董牧师,实为潘汉年的得力助手,他以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,秘密从事地下工作。1933年,潘汉年将董牧师介绍给了宋庆龄女士。此后,延安方面曾告知董牧师,如有资金需求,可直接向宋庆龄女士借贷。董牧师曾多次前往莫里哀路拜访宋庆龄女士,并向她提出,需要经费以支持几部电台的正常运行。每逢宋庆龄都会尽力满足他的请求,当然,这一切均出自她个人的财力。“董牧师”的频繁索求资助,令宋庆龄心生不悦。随后的日子里,王明自莫斯科发来电报,指示宋庆龄不宜再与董牧师有所往还。换言之,便是停止对他的经济援助。至于董牧师所借之款,至今未曾归还宋庆龄。
董牧师维护的不只是电台。宋庆龄与莫斯科之间的通信同样依托于这些电台完成,负责传递电报的正是董先生的女儿露西。董负责管理一所名为“大同幼儿园”的机构,该园接纳了众多革命世家的后代,其中便包括毛岸英、毛岸青等幼童。随着岁月的流转,那所幼儿园不幸宣布解散,至于其背后的原因,是因国民党所致还是资金短缺所迫,真相已随时光渐行渐远,无从稽考。
关于潘汉年处理的巨额资金,是否属于宋庆龄的私人财产?在“文革”落幕之后,母亲所在单位将她那段时期所撰写的交代材料悉数归还。我在翻阅母亲的这些材料时,偶然发现了一段文字:
“自解放以来,潘汉年曾向宋先生归还了一笔款项,据传这源自‘主席曾委托她向其兄弟借款’。”
然而,鉴于宋先生素来未曾向她的兄弟借款,无奈之下,只得将位于上海莫里爱路的住所进行典当,以此满足“主席之命”的要求。
此文档编制于1969年3月18日。其内容当然并不仅限于所述事件。当时,母亲在单位需每日撰写交代材料,有些往事因久远而记忆模糊,便需详加核实后方可落笔。3月18日所撰材料,开篇便提到:“在上文材料(即前一天所交代的内容)完成后,鉴于丁同志的特别要求——‘具体时间、具体人物’,我收到了宋庆龄先生的回信。因此……”。在撰写交代材料的同时,母亲还需向宋庆龄女士进行核实。鉴于新中国成立前母亲曾伴随宋庆龄女士工作,诸多往事均与之息息相关。此次交代材料正是因为涉及1941年在香港,母亲陪同宋庆龄女士前往码头取回一箱美元现金一事,故而写信向宋庆龄女士进行核实。在如此情境下所书写的文字,理应不存在虚假之处。
此外,宋庆龄在1969年致我母亲的信中提及,那笔钱是她过往生活的经济来源。李云,曾作为潘汉年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人,在其文章《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》中提到,新中国成立前,宋庆龄“仅依靠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抚恤金的利息维持生计”。那么,这笔抚恤金的总额是多少呢?在1974年4月25日,宋庆龄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及了相关信息。
“当您的父亲不幸遭遇暗杀,我曾在上海致信广东,表达了对他的家人应享有与我同等待遇的坚定立场。我的弟弟宋子文曾来信告知,国民党政府依照规定,向您的外婆何香凝颁发了五万广东省币的抚恤金,数额与我所获一致。”
我的工程师姑父在1932年于广州独立设计并建造了一座三层小洋房,其面积约为170平方米,花费了一万省币。姑父当时的月薪并不低,为200省币。五万省币的金额相当于他二十年的工资。由此可见,五万省币并非一笔小数目。因此,宋庆龄依靠这五万省币的利息维持生活是完全可行的。这也是她信中所提到的“以往赖以为生”的经济来源。
尽管宋庆龄将所有抚恤金悉数用于其中,仍与五万美元的目标相去甚远。以1936年的汇率计算,美元兑法币的兑换比例为1比3.77,这意味着一美元可兑换3.77元法币,故五万美元约合十九万法币。而广东省币的比值更是略逊于法币。正因如此,她不得不将位于上海莫里哀路的房产进行典当。根据上述两份材料,我们可以推断出宋庆龄所提供的巨额资金系其私人财产。

宋庆龄在毛泽东提出资助要求的一个月内迅速筹措到资金,有说法猜测这笔款项可能与共产国际有关。确实,宋庆龄过去曾代共产国际向中共输送过资金。然而,若资金源自共产国际,为何潘汉年会将钱归还给宋庆龄,并声称是“毛主席请她向宋子文借款”呢?共产国际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一直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,并无“还款”之理。宋庆龄退还此款后,不久便再次收到。这进一步表明,资金实为宋庆龄个人所出。
在线配资论坛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在线股票平台吸引着大批市民与游客在此领略啤酒节的“醉人”热情
- 下一篇:没有了